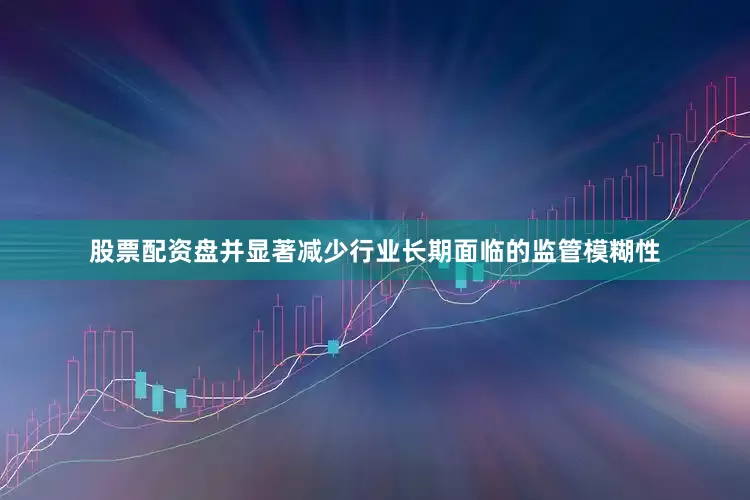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,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。

刘攽和的关系非常好,您知道王安石这个人私底下就不太喜欢和人聊天,性格比较高冷,但是只要见到了刘攽,那就是相见如故,一聊就是一整天。
王安石做参知政事,就是副宰相的时候,有天在家吃饭,饭吃了一半,刘攽就跑到王安石的家里去找王安石聊天,王安石说我吃饭呢,等我吃完我跟你聊,于是王安石就让家里的仆从把刘攽迎到了书房,仆从给他沏上热茶,送上点心,仆从就走了,刘攽就在王安石的书房中小憩,稍作等候。
王安石的书房,很雅致,布置的很不错,刘攽转悠来转悠去,就转悠到了书桌上,他一眼就看到,砚台的下边压着一张纸,拿起来一看,原来是王安石写的一篇议论军事的文章。
文章好坏咱们先不说啊,咱们且说,刘攽这个人,他记忆力非常强,但凡是文章书籍,只要看过一遍,必然过目不忘,所以两三分钟时间,他就把王安石的这篇文章给背了下来,背完之后,他就把文章又放回砚台下边,当做自己从来没动过。
接着书房他也不待了,因为他觉得,书房是很私人的地方,自己也是朝廷官员,以朝廷官员的身份来拜访王安石,最好还是在比较公开的地方交谈比较合适,就算主人让他待,他也觉得不合适,所以他就退出了书房,在廊下等候。
王安石跟刘攽感情很不错,刘攽一来,他怕故人久等,赶紧扒拉饭,风卷残云一般吃完了,立刻到廊下和刘攽攀谈起来。
两个人相谈甚欢,谈天说地,聊了一会之后,王安石就随便问,说老刘啊,最近写没写文章啊?
刘攽则说,真巧,自己正好写了一篇文章,叫做《兵论》,是议论军事的。
刘攽说完这一句,又接着把《兵论》中的内容全都陈述给王安石听。
其实,刘攽最近根本没写文章,他说自己写了《兵论》,还长篇大论的讲给王安石,其实就是他刚刚在书房里看到了王安石那篇论兵的文章,他背下来了,他就当成自己的讲给王安石听。
那正常来讲,王安石肯定会认为是刘攽进了他的书房,看了他的文章,所才说了他的词,但是古人的思维和我们的思维不尽相同,王安石只会觉得,刘攽是不会乱动乱碰,更不会去阅读自己已经压在砚台下的文章的。
所以王安石就感觉,自己对军事的看法,和刘攽的相同了,搁今天话说就是撞衫了,所以刘攽走了之后,王安石非常不开心,他把那篇文章从砚台下抽了出来,撕了个粉碎。
为什么呢?因为王安石这个人呐,平素追求标新立异,总是要发表和别人不一样的见解,如果有人和他见解相同,他就会认为这个见解,是庸俗的,所以他才会如此难过。

又有一回,王安石和刘攽聊天,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的时候,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,那就是他要大力的发展经济,他要挣钱,所以他平时很喜欢谈论生财之道,民间有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抓住了王安石的这个心理,就找到王安石,说大人我有一计,把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排光,然后把这块土地改为田地来种植,那一定能赚不少的钱。
水泊梁山,就是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境内的一个地方,《水浒传》里宋江起义之所。
王安石一听,认为这是个好办法,非常的开心,但他随即想到一个问题,他就一边思考一边念叨,说把水泊梁山的水排光了改为土地,用来种地,这倒是好办法,可是问题是,排出来的水要放到哪里呢?
当时刘攽正好在王安石身边,刘攽当即说道:
那还不好办么?在水泊梁山的旁边再挖一个八百里的大坑,把水排进去不就得了。
王安石一听,哈哈一笑,知道刘攽是在笑话他,终于打消了这个想法。
争论以智慧收场,而非权力压制,无论如何,宋代的士大夫,还是拥有更为理性的传统。
刘攽是北宋人,庆历年间的进士,地方上做过知州,官职最高到中书舍人。
当然他有段时间还负责编修国史,所以他也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。
编修国史的时候,刘攽有个同事,叫做王汾,俩人是平级。
可是有一天,刘攽却跑到王汾的家里,毕恭毕敬的拜见王汾,说王大人,祝贺你啊,你该换新官服了。
换新官服的意思就是,刘攽说王汾升职了,升官了。
刘攽来祝贺王汾,王汾则是一头雾水,他说刘大人您这是什么话啊,你祝贺我升官,可是我从来没有得到升官的消息啊。
刘攽说那不对啊,早上閤门使,也就是负责宫廷礼仪传达的官员已经通报了消息,您还是赶紧去问问他吧。
王汾一看,这刘攽不像是开玩笑,立刻就跑到宫里去询问閤门使,结果閤门使也是一脸懵,说我从来也没得到过旨意啊。

王汾又问,让我升官的旨意没有,那有没有别的旨意?
閤门使说,别的旨意倒是有一个,那就是皇帝今天放出一个命令,这以前吧,咱们大宋朝的王公勋贵的坟墓,不允许用红色作为装饰,但是现在皇帝说可以了,可以让他们用红色来装饰墓室,也可以用红泥来涂抹墓墙。
王公勋贵的坟墓,简称王坟,这个时候王汾才明白,原来刘攽是在戏弄他,人家皇帝明明说的是王坟可以添红,王坟和自己的名字王汾同音,刘攽就拿谐音梗来诓骗自己升官了。
刘攽还爱好写诗,和苏轼也有往来,并且关系匪浅,还因为同苏轼唱合诗作而获罪,当时苏轼反对新法,被贬谪流放,跟苏轼有来往的人,苏轼的好朋友啊,都跟着吃瓜落,刘攽也是其中之一。
后来到了元祐年间,两个人又都返回了京师为官,而且还是在一个办公室里。
所以刘攽和苏轼就经常闲聊,有一次刘攽就跟苏轼讲了一个故事,说以前,有一个盗贼,他闯入了一户百姓家中,没偷别的,只偷走一卷书就跑了,这书呢,是一个举人写的,里边基本上就是五言诗,七言诗之类的。
这盗贼偷了书,就拿到当铺里去卖,当铺的老板呢,他知道这个人是盗贼,但是他没有声张,而是把书收了下来。
为什么呢,当铺老板也是个读书人,识货,他一看这书,这诗集写的挺好的,他就买来收藏了。
结果,第二天这盗贼就被抓了,被抓之后,自然要供认偷盗的书籍销赃何处,衙役们直接就找到了当铺,从当铺老板的手里把这本书拿走了。
书倒是不值钱,但是属于赃物,必须收掉。
可这当铺老板啊,也是一个痴人,他竟然花钱贿赂衙役,只求可以在书被没收前,抄录一下其中的内容。
当铺老板说,我太喜欢这些诗了,想自己也写诗,顺便和书中的诗一同唱和,用现在话来说等于是同人或者二创。
结果,这个请求被衙役拒绝了,衙役的理由是,这是贼赃的诗,不能唱和。
刘攽的这个故事,其实意有所指。

这本书中的诗,指的就是苏轼的诗。
而当铺老板想要抄写这些诗,其实就是在影射自己当年唱和苏轼的古诗而被连累处罚。
衙役说,赃物诗不能唱和,其实就是在暗讽苏轼的诗水平平庸,根本用不着唱和。
刘攽说完,苏轼也给刘攽讲了一个故事,苏轼说,孔子当年有一次外出,他的弟子,一个颜回,一个子路正巧远远看到孔子走过来,两个弟子不去拜见老师,反而连忙躲避。
子路的身手比较敏捷,一下子就爬上了树,而颜回就比较慢了,环顾四周,他无处可藏,只好跑到一处石经幢后藏了起来。
石经幢,就是一种刻有佛经的石柱。
孔子没有发现这两个弟子,顺着道路逐渐走远,但是颜回藏在石经幢后的事情,很快就传开了。
大家就议论,说这个石经幢啊,被颜回当做躲藏孔子的柱子,那就有了特殊的意义,所以不能再叫石经幢了,而应该叫做避孔塔。
苏轼为什么要说这个石经幢被叫做避孔塔呢,很简单,因为避孔塔的谐音就是鼻孔塌,而当时刘攽正好患了一种病,这种病就导致他的鼻子是塌陷的,苏轼是借着这个谐音梗来嘲笑刘攽,顺便还以颜色。
其实这也是宋代文人的一种生存智慧,用典故和幽默化解政治创伤与疾病折磨的痛苦。
这些看似轻松戏谑的轶事,如同一扇窗户,让我们得以窥见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斑斓一角。
在刘攽与王安石,苏轼的交往中,我们看到的远不止文人的雅趣与机锋,更能区别于传统叙事,看到古人更为真实生活的一面。
读这篇文章,我们感觉刘攽是个怪人,做事比较不守规则,还有点叛逆,但其实他一生潜心史学,治学非常严谨,这又着实让人想象不到了...
参考资料:
《东轩笔录》
《后山丛谈》
李全德.《资治通鉴》长编分修问题新探.史学史研究,2025
王艳军,朱富铭.论苏轼与元祐秘书省职官的诗歌唱和.河北经贸大学学报(综合版),2024
永华证券-永华证券官网-上海股票配资平台-广州股票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杠杆平台美国的建筑支出和设备采购数据疲软
- 下一篇:没有了